我想我是病了,这次我希望自己大病一场。
耳鸣、太阳穴跳着疼,浑身散架、脖子、脊椎好象拧了,动起来都困难,脑袋里
象是灌了泥浆,昏昏沉沉的,四肢无力,怀疑自己还能不能举起一盆水,然后倒
在地上。
上海的阳光暧昧而温暖,照着我胳膊上戴着的黑纱,我想妈妈。
18号冒雪回家奔丧,在母亲灵堂前磕着响头,失声痛哭;太平间里很冷,想着母
亲躺在冰冷的地方,我不愿意穿家里为守灵准备的军大衣;捧在母亲的骨灰盒上
山,头七时候去墓地给母亲祭献花篮,再冷也不愿意戴手套;母亲的瘁然离世让
我痛苦万分,也令我内疚万分,我想通过惩罚自己获得一些平静和安宁。
此刻,我很虚弱,虚弱得象个孩子。
早晨丹琳给我短信,他们八点半吃完解放军做的热面条已经出发,昨天晚上他们
宿营在部队的养殖场里;想着他们的辛苦和艰难,很想去追赶他们,但是还有一
些事务羁绊着我,只能滞留在这个我并不喜欢的国际化大都市里。
望着前方未知的岁月,这次我会大病一场吗?而病愈之后,我还有力气背着行囊
,走在朝阳与落日之间,行在黄河和大漠的边缘吗?
百折不挠、积极进取、勇往直前,我还会矢志不渝地实现吗?
很多年前,我想象过自己老成一片落叶的样子,大病之后,我会是一片衰老的叶
子,叶落归根吗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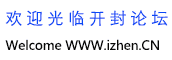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06-01-25 13:30:10 [显示全部帖子]
Post By:2006-01-25 13:30:10 [显示全部帖子]
